《安妮特》剧情介绍
安妮特电影免费高清在线观看全集。
讲述一对好莱坞夫妇和他们的女儿安妮特的故事:丈夫亨利(亚当·德赖弗 Adam Driver 饰)是一位单口喜剧演员,妻子安则是一名歌剧明星(玛丽昂·歌迪亚 Marion Cotillard 饰),而他们神秘的女儿安妮特,又拥有怎样不同寻常的人生呢?热播电视剧最新电影鲜血淋漓第二季坦白一个父亲的寻肝之路冰冻之河IRIS泥土之界青春王室第三季败犬女主太多了!好日子别不好好过氧气危机恋上女镖师旅“奥”一家人热血军旗白夜权力的游戏第八季你来自哪颗星正义联盟:无限地球危机(上)马普尔小姐探案第一季蜜蜂少女队3迪兹先生绝杀慕尼黑震天鼓枭雄爱的沉浸式占领区第一季恋爱细胞第2季大婚告急江南1970山花绽放P与JK
讲述一对好莱坞夫妇和他们的女儿安妮特的故事:丈夫亨利(亚当·德赖弗 Adam Driver 饰)是一位单口喜剧演员,妻子安则是一名歌剧明星(玛丽昂·歌迪亚 Marion Cotillard 饰),而他们神秘的女儿安妮特,又拥有怎样不同寻常的人生呢?热播电视剧最新电影鲜血淋漓第二季坦白一个父亲的寻肝之路冰冻之河IRIS泥土之界青春王室第三季败犬女主太多了!好日子别不好好过氧气危机恋上女镖师旅“奥”一家人热血军旗白夜权力的游戏第八季你来自哪颗星正义联盟:无限地球危机(上)马普尔小姐探案第一季蜜蜂少女队3迪兹先生绝杀慕尼黑震天鼓枭雄爱的沉浸式占领区第一季恋爱细胞第2季大婚告急江南1970山花绽放P与J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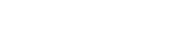
木偶小女孩可真恐怖。只有最后一段父女相对唱歌的戏喜欢。
卡拉克斯瑰丽的开场即已预示了摄影机的回归、电影的回归。安妮特像是聚光灯下产物,时刻得进行着表演,所以在此之下的她一直呈现着木偶状,而当她卸下了人们的“注视”后,终于现回了人身。电影也是如此,在进行了一切的提纯后,回归了它本身:电影就是为大银幕所生。由“May we start?”开始,我们已做好迎接这枚属于film的炸弹响起。
莱奥斯·卡拉克斯鸣谢埃德加·爱伦·坡
3-,也就是人的失落、失望、失控,毁灭之路。形式既不讨喜也不凌厉,不好看也不能突显主题。女人咬苹果,男人脸有疤。
3.5/ 卡拉克斯在視聽方面確實做得很出彩,用迷人的佈景和實景,鮮明詭譎的色彩,精心設計的燈光和鏡頭,遊走自如的空間切換和調度,等等都在竭力打破電影與戲劇的邊界。可同時,敘事上卻用了一個古典到有些過時的故事,與整套視聽的探索呈現出了一種背道而馳的趨勢,互扯對方的步子。我就在想,同樣的劇本如果放在劇場裡,配以現在的表演佈景燈光等等,但拋掉那些空間和形式探索,我依然會覺得是一出精彩的舞台劇/音樂劇,古典到過時也好,甚至是劇情發展上的不自然和人物塑造上的不完整,好像都能被原諒,至少不會成為一個減分項。那麼將戲劇電影化的意義到底在哪裡呢?吸引人的到底是電影本身還是一種實驗造成的奇觀呢?(ps,人偶太嚇人了 以及 司機太帥了)
三星半。之后会再对看神圣车行。除了难以避免地将德赖弗的表演与拉旺作比,还有些点让我觉得它“好却又没那么好”是在于,故事本质上其实非常古典(不知可不可以视为法语片转向英语片中“神秘性”的失落),因此在用超现实手法讲诉现实主义的故事时,形式与内容应要寻找到更有机的结合方式,而仅是套用歌舞片或音乐剧的样式显然不太足够,除了作为取消叙境内外界限的间离化手段外,总是缺点意思(尤其,这可是卡拉克斯啊不是吗)。嗯,必须要说的是,最喜欢的是那份自指,卡拉克斯在一开始就以拒绝缝合的姿态现身,直到最终完成从个人性到私人性的跃升,我觉得这是最动人的部分。
四星半。脱口秀喜剧演员与歌剧演唱家的悱恻爱情,缔结出怪诞之女安妮特,莱奥·卡拉克斯将一出三言两语便能说透的世俗往事,激活为天马行空的墨绿警世寓言。叙事的过程,成为各色舞台表演形式呈现的通渠,调度极尽复杂之能事。火花兄弟的作曲更成为影片的灵魂挽歌,在亚当·德赖弗声台形表样样通达的发挥下,令心酸成为终极魅惑。
不记得之前看没看影片简介,开场就觉得很惊喜,看到十几分钟才发现原来是个音乐剧式的电影。不过越往后看越没有那么兴奋了,音乐和男主的演唱算不上特别高水准,好在有不少段落挺有趣的。很喜欢安妮特的木偶,虽然诡异但富有人性,也起到了某种连接观众和戏剧的作用。(除了她和安的发型让我想起了美柳千奈美,有点害怕。)不管怎样,假期第一天结束了。而滞留北京的春节生活才刚刚开始。但愿朋友聚会,电视剧和游戏能拯救我~
对于一个此前没看过卡拉克斯的人来说,他真是把电影玩弄于股掌之中。(结尾致谢名单还有爱伦坡和金维多)
卡拉克斯居然还活着!我请你陪我七块电影票钱以及三十块啤酒钱 I’d have walked out of the theatre without the four beers..
我看不懂但我大受震撼。倒是挺喜欢这种音乐剧的形式。依旧是模糊现实与舞台的边界但卡拉克斯走得更远。色彩还有唱段都表明这是一部形式感非常强的电影。提线木偶有一天也会有自由意志。8/10
2024-11-19:够先锋,够独特,够邪典,把传统的音乐剧完全融入电影并加入冒犯讽刺和符号学。为什么喜欢这部电影?我也不知道。从这之中感受到了什么?我也不知道,只能说在直观感受上就给我很不错的体验了。观感写了两天,实在是太过于复杂难以表达,又去看了很多解读,不过有一点,我根本没看出来这么多夸张与复杂的内容。整部电影视听与调度都太过丝滑让人舒爽。不得不说这么自恋变态的男主形象真的很适合我并不怎么喜欢的司机大叔。对于观众千篇一律反应是极其冒犯的,但是对于一个自毁倾向极为严重的导演以及他半自传体式的电影来说,他对于自身的厌恶似乎远超与对于观众的厌恶,所以反而会得到谅解与同情。结尾处“凝视深渊”我很难说不喜欢,但就是觉得太过于生硬和直白。以及,很多情节之间太过于断裂。
不管形式是不是有效(IMDB首赞评论:像一个努力先锋的学生作品),故事也太toxic了(如果虚构那就是人物有毒,如果自传那就是个毒王,顺便把全剧组搞成cult)。永远放浪形骸,永远八块腹肌高大威猛;醉酒家暴杀人变成海上的一场风暴(内因扭转成外因);这有什么好abyss的,主角是别人的深渊才差不多。(司机长得好像山顶洞人
卡拉克斯拿金棕榈没戏了
实在无法忍受手握资源的一帮电影人,浪费那么大人力物力去拍这么点破事儿。作为一部歌舞片写的旋律折磨耳朵,叙事乏味而催眠,整体几无深刻可言,风暴与女儿不再是木偶的明喻无甚高明,一群人逮着一颗女主吃的苹果分析半天。亚当德赖福这两年活像好莱坞的大景甜。与此同时有多少好故事因找不到资方夭折。
半吊子蒂姆伯頓。結尾結得尤其弱。
驾驶摩托车消失在《妖夜慌踪》的黑夜,滑进《日出》和《郎心似铁》的深渊。《神圣车行》的大幕再次拉起,卡拉克斯的替身亨利登场,电影回来了。 9.0/10
2021戛纳最佳导演奖。元·musical,比起“歌舞片”更准确是“音乐剧”吧,虽然明显看出卡拉克斯老了且疲惫了,不过许多地方还是蛮讨喜的:开头+开场唱段满分,观众歌队化不错,老司机够拼,苹果/苹果手机,木偶/女儿这套喻体也有意思,结尾谢幕好动人(甚至觉得卡拉克斯就此息影了也挺OK……)
歌是真难听啊!
核心即空心 神圣车行也是相同的主题 但后者实际上还是突出了男主/Lavant作为魔法师的力量 表演在数字时代被赋予了新的角色 即它具有超越简单实指的魔法效力 而这个主题在本片则完全被等同于showbiz的虚无。这种空洞在表达形式(音乐剧与多种浮夸无必要的画面组合形式)本身的虚无化加持下一路坠落 绿色-统一和声的观众像是僵尸一般参与到这场演艺圈自我摧毁的盛宴中。司机可能是当下最无聊的演员了 似乎就是一个情绪机器 剥掉浴袍便什么都没了 他在这里跟婚姻故事有毛区别?都是一幅Kylo Ren的样子。我比较感兴趣女主的大都会式的车子和无限延伸的舞台 但很快就没了 完全被男主的绿色调抑郁白男自暴自弃气息吞噬。另外最后体育场表演那舞台是致敬恐龙战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