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巫》剧情介绍
南巫电影免费高清在线观看全集。
1987年马泰边界,吉打象屿山下的村落里,村民阿昌是民间神明拿督公的虔诚信仰者,妻子阿燕却不以为然。某日阿昌驱赶神龛前的蛇,不慎打破暹罗裔邻家屋墙。两周后,阿昌突在田埂晕阙,口吐血丝锈钉,村人知悉各圆其说,阿燕全然不信,决意为丈夫遍寻药方。三个月后,阿昌久病不愈,阿燕无计可施,到洞穴祭拜象屿山神。此时,穴内出现一名女子,向她娓娓道出狼牙修时代的传说。霎时之间,阿燕仿如置身边界的融汇与对立,深陷惶恐与未知。本片以精湛的视听语言和炉火纯青的场面调度勾勒出东方神秘主义的新面貌。热播电视剧最新电影放飞哎呀妈妈不完美的美烈血暹士2空战魔导士候补生的教官家庭时间方小姐的恋爱秘籍艾达·雷德美好事物哈啰义乌神枪少女无畏上将高尔察克纹身李卫当官薛仁贵传奇女人置上拯救爱情希区柯克孤独的美食家2023除夕特别篇特种兵归来1:血狼之怒哺乳期的女人万物商店之木偶杜兰餐馆:黑色传奇五卢比恩仇录大都市爱情法坏牧人港湾第二季金之国水之国刀手与卿行
1987年马泰边界,吉打象屿山下的村落里,村民阿昌是民间神明拿督公的虔诚信仰者,妻子阿燕却不以为然。某日阿昌驱赶神龛前的蛇,不慎打破暹罗裔邻家屋墙。两周后,阿昌突在田埂晕阙,口吐血丝锈钉,村人知悉各圆其说,阿燕全然不信,决意为丈夫遍寻药方。三个月后,阿昌久病不愈,阿燕无计可施,到洞穴祭拜象屿山神。此时,穴内出现一名女子,向她娓娓道出狼牙修时代的传说。霎时之间,阿燕仿如置身边界的融汇与对立,深陷惶恐与未知。本片以精湛的视听语言和炉火纯青的场面调度勾勒出东方神秘主义的新面貌。热播电视剧最新电影放飞哎呀妈妈不完美的美烈血暹士2空战魔导士候补生的教官家庭时间方小姐的恋爱秘籍艾达·雷德美好事物哈啰义乌神枪少女无畏上将高尔察克纹身李卫当官薛仁贵传奇女人置上拯救爱情希区柯克孤独的美食家2023除夕特别篇特种兵归来1:血狼之怒哺乳期的女人万物商店之木偶杜兰餐馆:黑色传奇五卢比恩仇录大都市爱情法坏牧人港湾第二季金之国水之国刀手与卿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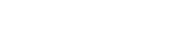
以一种乡村写实的方式去拍了一个神秘巫术的故事,童年回忆,固定镜头与长镜头,所以在前面三十分钟,会误以为这是一部乡愁与回忆的影片。整部片子很克制,没有过多情节渲染巫术与神秘,更是氛围吧。比较有意思的,还有背后的一些背景,感觉还是有些马来华人的身份认同或文化诉求在里面。比如1987年这个时间设定,刚好是茅草行动,影片中也提到非华人出任华人学校高层这个新闻,以及孩子桌上的爪哇课本。再对比片中那些信什么神,说什么话的对比,会对影片有更多理解。
#張吉安導演影後談。導演自言:1. 電影中八成都是真事,包括父親吐釘、車頂出現怪聲;2. 關於邊界的故事,語言、民俗、種族間都有邊界;3. 靜鏡頭、長境頭受小津、侯孝賢影響,部分鏡頭設置得很低,是希望從萬物之靈的角度觀照人間(當地人相信萬物皆有靈,例如蛇、昆蟲、稻、石頭……);4. 深夜稻田中的「舞」是導演本人所編舞,舞者是舞蹈表演的教授;5. 定位從來就不是恐怖片。#26.9.2021香港藝術中心
水田中的男子,总感觉有个男网红已经提前拍过了
调度有点东西,喜欢从边缘视角切入一场戏,或远处旁观,增强纪录感和沉浸效果,但拍的东西实在意思不大,有点浪费了好调度。导演是真的喜欢稻田芦苇田,但这些镜头加进来是真的没啥用。女主角的形象有曾美慧孜的意思,去除了情欲部分,她的眼睛非常好看,一眼能看出善良、脆弱、有点呆板的愚昧,一个深山里的弱势妇女,她给人的感觉跟最后湖上漂泊的孤舟的意境异曲同工。
四不像文艺鬼神身在异邦苦难片。后面几分钟略瘆人。扒车那位让我想起了Sopor Aeternus
坚强的女性
身份认同的感觉,不了解文化背景,不好评论。至于恐怖不恐怖,肯定是不吓人的,可能大多数观众反而会昏昏欲睡。
除了摄影,可以说一无是处,怎么被吹成这个样子?
作为民族志的表达多过电影表达 映后谈说得比拍得好个人魅力加一星 导演对记忆的忠诚、对华人离散史和社区参与的执着令人尊敬 他说80%是真实 我更喜欢那20%的轻盈 鬼灵具像化成舞踏的想法很喜欢
马来巫术战降头,用写实的手法拍出的巫术原来是这样,几段巫术的呈现方式,皮影戏、山神婆婆、人形的神、招魂、骑象人。zz隐喻没看懂,就是觉得好文艺,一点不惊悚。胆子小故意选了日照三竿阳气最旺的时候来看,duck不必,没问题晚上看也不吓人。
没看下去。。
去年的金马奖最佳新导演,处女作还是有想要讲太多却都表现得不太到位的感觉,而且儿时记忆加田野调查也使故事拼凑感很强。女主很耐看有气质,一查果然选美出身,不像属于那里的人也达到了从不信到相信并目睹古老的巫术和传说的效果。与蔡明亮合作过的女配那段、小鬼出现的几次还都挺瘆人,国歌、改名、讲华语、皮影戏、向往泰国、种族信仰、身份认同等细节都很有意思,马来西亚80年代末的乡下生活也看着比我小时候好得多呀。很喜欢最后在船上突然诉说华人远渡南洋后不能越过的边界,以及送给父母致敬电影前辈的字幕。非常值得一看,毕竟我们这里拍不了这样的题材。林象朗园导演张吉安映后视频连线。
像当年看陈英雄的爱情片,时不时地想昏睡过去。。。叙事假借一个华人移民家庭的文化调和,又是曾经引致商业噱头的南洋降头元素,但不是猎奇式的大赏,形式呈现一种平静而沉闷的诡谲气氛,联想片中背景其实不难明了说的是华人移民与马来当地文化的交融问题。手法很是独特,确乎异于日韩泰港的鬼片。假如毕赣拍鬼片一定是这般调性。7
3.5,多亏影评区的解析,不然真看不大懂
东南亚华人的传统的迷信氛围渲染得到位,但实在无法共情,看不出群体的无奈和身份认同的困境,全片有着那股子无病呻吟的劲儿
以恐怖叙事包装,剧作布局精巧,对“降头”的描写既写实又轻盈,引领观众的猎奇心理。中蛊的源头做了减法,应当始于阿南母亲的疑心作祟。于是乎,“降头”带有象征意味,表象下是人与人之间信任的流失,包括将信将疑的阿燕,也游走于“医”与“巫”之间,直到她从信仰中寻求慰藉,观众也与之达成共情。她似乎也找到了某种身份认同——“永远过不了这边界,回不了我的老家”一语双关,也是一语成谶。
拿导演类奖很对。最直观的感受是,几乎所有技巧和方式的选取都是准确的,虽然有些固执。相对于人,似乎对物体更感兴趣:谨慎地保持着安全距离,但不断抛出道具进行交互。魅力还是更多源自原生环境,很不普世的创作方式。
导演给盗版者下降头这种做法很明显表明,哪有什么鬼不鬼的,有的话他也叫资本主义
恐怖片拍出了纪录片的感觉,带着作者的成长记忆,带着多元民俗文化的交织,带着沉闷和平淡。
搅乱边界的过去与现在 抵达分割人物的过去与现正在 那么至此语言、巫术、政治身份、文化认同、离家故国都聚集在这个地理锚点边界海域 窥探了时光和世事的缝隙